“给老板家孩子辅导作业算‘家庭教育辅助岗’,帮全组取外卖叫‘线下履约协调’,连拆几百颗文件钉子都能包装成‘文档优化与安全处理’—— 现在的实习生,早就把‘屎上雕花’的技能点满了。”
打开社交平台,关于实习生 “dirty work” 的吐槽从未停歇。有人在律所实习三个月,没见过案卷却成了 “全职茶水师”;有人在互联网公司负责 “AI 无法识别的格式调整”,每天重复粘贴 500 次表格;更荒诞的是,某广告公司实习生被要求 “观察同事穿搭判断谁在生理期”,理由是 “方便行政调整下午茶温度”。这些听起来像段子的经历,却是当代实习生的日常。当 “整顿职场” 的口号遇上现实的 “脏活”,00 后们究竟在经历怎样的职场初体验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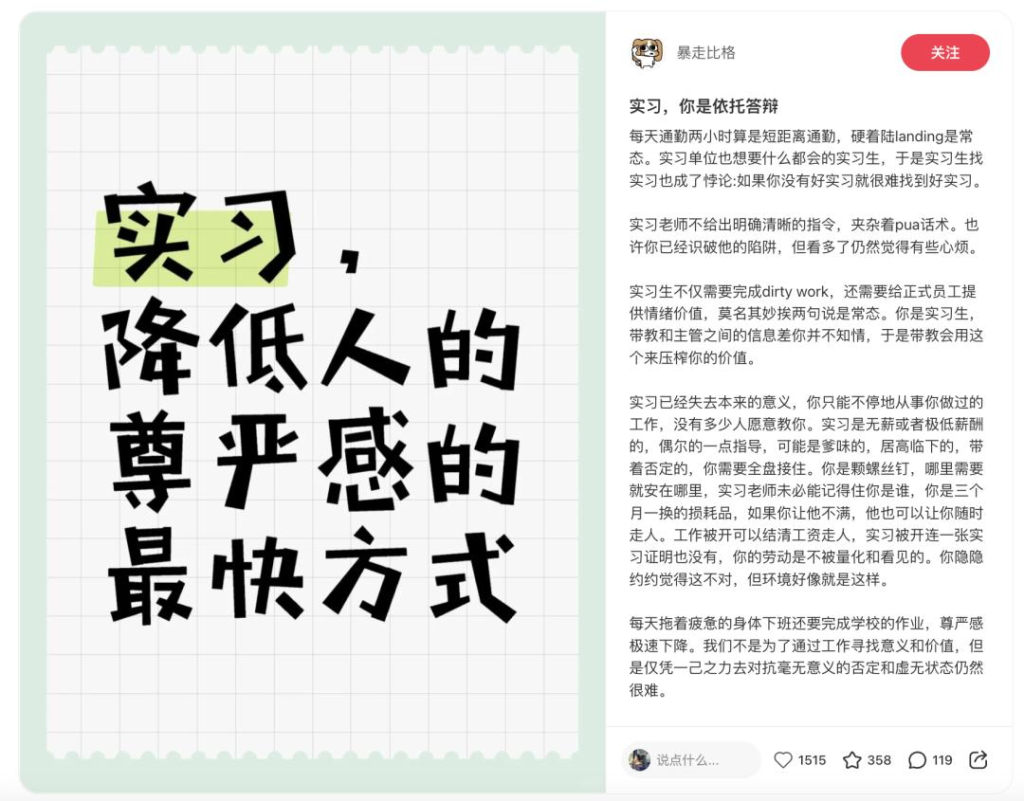
“脏活” 进化史:从带薪实操课到无薪打杂工
现代实习制度的诞生,本是一场 “教育与产业” 的美好联姻。20 世纪初,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 Herman Schneider 提出 “交替式教育”,让工程专业学生一边上课一边在工厂带薪工作,既能将理论落地,又能为企业输送技术人才。那时的实习是 “双赢” 的:学生在机床前学习操作,在实验室参与研发,哪怕做的是基础工作,也能触摸到行业核心;企业则用较低成本培养未来员工,避免了 “毕业即失业” 的人才浪费。
但从 20 世纪后期开始,实习逐渐变了味。随着大学入学率激增,美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在 1970-1990 年间翻了三倍,而优质岗位增长却不足 50%。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,学生不得不通过实习积累履历;企业则敏锐地发现,与其花高薪招聘正式员工,不如用 “学习机会” 为诱饵,让实习生承担没人愿意干的杂活。于是,实习从 “带薪实操课” 沦为 “无薪打杂工”,“dirty work” 也从偶然的辅助任务,变成了实习生的核心 KPI。
这种变化在国内同样明显。十年前,互联网行业处于高速扩张期,实习生哪怕做的是边缘工作,也能参与核心项目:帮产品经理整理需求文档,可能顺便学到用户分析逻辑;给运营团队打杂,或许能接触到活动策划全流程。但现在,行业进入存量竞争,正式员工的工作都围绕 “反复优化功能”“精细化修报表” 展开,留给实习生的,自然是更琐碎、更无意义的 “脏活”—— 复印文件、贴发票、统计数据、甚至帮老板处理私人事务。
更讽刺的是,企业还为这些 “脏活” 发明了各种 “黑话包装”:把 “人肉传话筒” 叫 “部门信息中枢”,把 “格式调整工具人” 称 “文档标准化专员”,把 “帮老板跑腿” 定义为 “关键节点实体信息流协调”。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 title,终究掩盖不了 “重复劳动、毫无成长” 的本质。
AI 时代的 “脏活” 新形态:机器做 80%,人补 20% 的边角料
如果说过去的 “脏活” 是因为人力成本低,那现在的 “脏活”,还多了一层 AI 的 “推波助澜”。
哈佛大学两位经济学博士曾做过一项研究:他们追踪了 28.5 万家美国企业的招聘数据,发现自 2023 年 ChatGPT 走红后,部署 AI 的企业平均每季度少招 3.7 名初级员工,初级岗位招聘量缩减 22%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也显示,在 “高 AI 暴露职业”(如数据录入、基础编程、客服)中,22-25 岁年轻人的就业人数下降了 13%。AI 正在替代越来越多初级工作,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。
但诡异的是,AI 并没有消灭 “脏活”,反而把 “脏活” 变得更 “细碎”。在很多公司,AI 负责完成 “80% 的核心工作”:比如用大模型生成报告初稿、用算法统计基础数据、用工具批量处理文件格式。但剩下的 20%“边角料”—— 检查报告里 AI 写错的专业术语、修正数据表格中算法识别错误的单元格、调整文件格式里机器无法兼容的细节 —— 全都丢给了实习生。
某互联网公司实习生小周的经历很有代表性:她的日常工作是 “给 AI 生成的产品分析报告挑错”。AI 能快速整合用户数据、生成图表,但常常把 “DAU(日活跃用户)” 写成 “MAU(月活跃用户)”,把 “转化率” 算成 “留存率”。小周需要逐字逐句核对,平均每天要修改 300 多处错误,“感觉自己像个 AI 质检员,还是没工资的那种”。
这种 “AI + 实习生” 的组合,本质上是把实习生变成了 “机器补丁”—— 机器干不了的细碎活、容易出错的麻烦活、没价值却必须有人做的杂活,全由实习生接手。更无奈的是,这些工作既学不到核心技能,又无法体现个人价值,唯一的 “收获”,可能是练就了 “耐得住无聊” 的心态。
00 后的对抗:从 “战略性敷衍” 到 “自我定义价值”
面对 “脏活” 困局,00 后实习生们没有坐以待毙,而是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策略 ——“战略性敷衍”。
“不求留用的实习生,地位堪比副总”,这是某社交平台上流传甚广的段子,却道出了很多实习生的真实心态。既然实习只是为了给简历 “添一笔经历”,那干过就算 “精通”,听过就是 “熟练”:参与过一次会议,就能在简历上写 “深度参与部门战略讨论”;帮同事整理过数据,就能描述成 “独立负责项目数据支撑工作”。他们不再纠结 “能不能学到东西”,而是用最小的精力成本,为履历挣下一枚谈判筹码。
这种 “敷衍” 不是摆烂,而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。00 后是在素质教育中长大的一代,从小被教育 “要成为创造者、解决者”,他们期待的工作是 “实现价值、获得成长”,而不是 “重复劳动、沦为工具”。当理想与现实落差太大,“战略性敷衍” 就成了他们对抗系统的方式:你可以安排我做什么,但无法决定我是什么人;你可以给我派 “脏活”,但无法消耗我对自我价值的判断。
更有意思的是,00 后还擅长用幽默消解 “脏活” 的荒诞。他们把 “帮老板浇花” 称为 “办公室生态维护工程师”,把 “扫厕所” 调侃成 “办公环境优化专员”,甚至有人把 “给鱼接生” 写进实习日记,配文 “解锁跨物种护理技能”。这种自嘲不是妥协,而是一种态度:我承认在做 “脏活”,但我不会被 “脏活” 定义。
还有些实习生选择 “主动破局”。他们利用 “脏活” 之外的时间学习技能:帮运营团队打杂时,偷偷研究活动策划逻辑;给市场部整理资料时,主动分析竞品案例。有人在实习期间自学了 PS、Python,有人把整理数据的过程变成了 “数据分析练手”,最后带着作品集找到更好的工作。他们明白,“脏活” 是环境的限制,但不是自我成长的上限。
破局之路:我们需要怎样的实习?
实习生的 “脏活” 困局,本质上是 “教育期待、个人需求与企业利益” 的错位。教育告诉年轻人 “要追求价值实现”,个人期待 “通过实习成长”,但企业却把实习生当成 “廉价劳动力”。要改变这种现状,需要多方共同努力。
对企业而言,应该重新审视实习的价值。实习不是 “低成本打杂”,而是 “人才储备”。真正聪明的企业,会给实习生安排有意义的任务:让他们参与项目的某个环节,而不是只做边缘杂活;为他们配备导师,而不是让他们 “自生自灭”;甚至允许他们试错,而不是只要求 “不出错”。比如谷歌的实习生项目,会让实习生独立负责一个小型项目,最后在全公司汇报成果;微软则为实习生提供一对一导师,帮助他们快速成长。这些企业明白,今天认真培养实习生,明天可能就会收获优秀员工。
对学校而言,需要加强对实习的监管。很多学校把实习算做学分,却不管实习生做什么、有没有收获。未来,学校可以建立 “实习反馈机制”,定期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,对 “只让实习生打杂” 的企业进行公示;还可以与优质企业合作,建立 “实习基地”,为学生提供有保障的实习机会。
对年轻人而言,要理性看待实习。一方面,不要对实习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,刚开始做一些基础工作是正常的,但如果长期只有 “脏活”,就要及时止损;另一方面,要学会在有限的环境中寻找成长机会,哪怕是整理数据,也能从中锻炼细心和耐心,哪怕是端茶倒水,也能观察职场沟通方式。更重要的是,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—— 实习是为了积累经验、找到方向,而不是为了 “忍气吞声”。
不被 “脏活” 定义的人生,才更有力量
实习生的 “脏活” 或许无法完全消灭,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被 “脏活” 困住。就像那些把 “卖煎饼果子” 说成 “无麸质可丽饼主理人” 的年轻人,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,而是在宣告一种态度:我可以做平凡的事,但我有不平凡的心态;我可以身处底层,但我有向上生长的勇气。
职场从来不是一场 “忍受脏活” 的比赛,而是一场 “自我定义” 的旅程。今天你可能在复印文件、整理数据,但这只是你人生的一个片段,不是你的全部。重要的是,在做这些事的时候,你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,没有放弃学习和成长。
就像一位实习生在日记里写的:“我今天拆了 300 颗钉子,但我晚上学会了做 PPT。明天我可能还要贴发票,但我计划开始学数据分析。我知道现在在做‘脏活’,但我相信,这些‘脏活’终会成为我走向更好未来的垫脚石。”
不被 “脏活” 定义的人生,才更有力量。愿每一位实习生,都能在琐碎的工作中找到成长的意义,在现实的限制中保持向上的勇气,最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发表回复